获阿里CEO投资,被比亚迪选中,85后海归博士逃离智驾“死亡谷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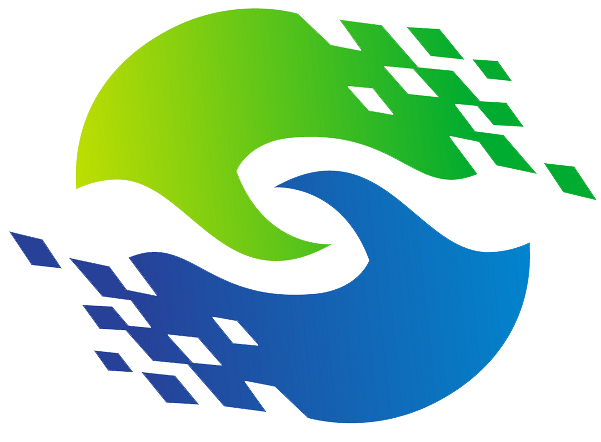 摘要:
春节过后,一些主机厂、供应链合作方经常到访公司,刘国清穿西装的频率越来越高了。“大家明显能感觉到今年被比亚迪卷起来了,有...
摘要:
春节过后,一些主机厂、供应链合作方经常到访公司,刘国清穿西装的频率越来越高了。“大家明显能感觉到今年被比亚迪卷起来了,有... 春节过后,一些主机厂、供应链合作方经常到访公司,刘国清穿西装的频率越来越高了。
“大家明显能感觉到今年被比亚迪卷起来了,有客户春节就给我打电话,让我们做好备料。还有想把交付时间往前提的,从12月提前到9月、10月,所以今年活儿肯定会很多。”刘国清对《中国企业家》表示。
2014年,刘国清回国创业,在深圳创立佑驾创新,聚焦智能驾驶和舱内解决方案。阿里巴巴集团CEO吴泳铭是佑驾创新的天使轮投资人,刘国清将之视为贵人之一。成立后十年间,佑驾创新先后获得10轮融资,吸引了四维图新、中金资本、元璟资本、普华资本、东方富海等投资机构和产业资本。
“智驾公司如果走不到盈利,很难走到终点。”刘国清说。
被阿里CEO选中
本科毕业后,刘国清前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攻读计算机工程博士学位。期间,他参与了由新加坡政府和南洋理工大学共同承接的ADAS(高级驾驶辅助系统)项目,并在CeMNet实验室担任视觉算法研究员。
这段经历,让他对ADAS产生了浓厚兴趣。2013年4月,刘国清和几位创始团队成员,决定回国创业。由于没钱、没资源,他们只能选择在距离南京市中心约70公里的高淳区做早期封闭开发,租了4间房,2个房间用来打地铺睡觉,2个房间写代码。用了8个月时间,他们开发出一款预警类手机APP“护驾”。
产品有了雏形,走出去找钱成为当务之急。但当时刘国清对融资一无所知,连商业计划书都不会写。他百度了一个模板,填了信息,就往各个投资机构的官方邮箱盲投。当时他看到网上报道称,“中关村创业大街的3W咖啡馆里,随便坐一个桌都能碰到投资人”,于是他和团队专门跑到北京碰运气。
后来,刘国清误打误撞参加了一个科技媒体举办的线下沙龙,结识了鼎晖资本的一个投资经理。对方说可以帮他推荐投资人,刘国清便把商业计划书发给了他。接下来的经历出乎他的预料:一天中午,他接到了前鼎晖创投合伙人李牧晴的电话,双方聊了大约20分钟,“他(李牧晴)觉得我们人挺靠谱,技术方向也不错,就说想把我们推荐给‘吴妈’(阿里巴巴集团CEO吴泳铭)”。
“国清能拉人、能攒人,CTO杨广曾是微信团队的开发工程师,获得过ACM/ICPC金牌,在智驾供应商里,还是非常少见的。”李牧晴告诉《中国企业家》。所以见面聊了一次,李牧晴就把这个项目推荐给了吴泳铭。
2014年9月,要赶去美国参加阿里上市敲钟仪式的吴泳铭带着两名技术专家,与刘国清在上海机场匆忙见了一面。在现场,刘国清展示了他们之前做的那款APP。据他回忆,吴泳铭觉得这个demo很有意思,很直观,也能充分展现团队的技术能力。
当时比亚迪使用的是赛灵思的一款芯片,但因产品功耗过高,无法量产。在发现佑驾创新也有类似方案,已经在出货且表现良好后,比亚迪紧急将佑驾创新拉过去交流,并让其迅速导入项目。
这期间,佑驾创新团队面临着巨大压力。从双方开始接触到量产上车,时间仅有半年。硬件设计方面,通常固定一版硬件需要3个月,之后还需要进行DV(设计验证实验,目的是验证产品设计是否满足功能和性能要求)、PV(生产验证,目的是验证产品生产工艺是否能够稳定生产出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)等实验。如果第一版硬件出现问题,再改版又需要3个月,这意味着佑驾创新必须确保第一版硬件就成功,后续最多只能进行微调。这对佑驾创新在软硬件一体交付方面的能力提出极高要求。为了按时完成任务,佑驾创新派出大量工程师驻厂,最终一次成功,守住了量产的时间节点。
这次项目锻炼了佑驾创新的交付能力。“那个时候真的是崩溃了,因为我本身没有硬件背景。”谈起这段经历,刘国清眉头紧锁,还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。当时这个项目打了三次版(打版,指样机制作与调试),等到了第二个、第三个项目,佑驾创新团队已经可以做到最多打两次版。“现在我们对硬件的要求是只能打一次版,如果打两次版,可能就要面临考核了。”刘国清说。
资料显示,目前佑驾创新已与上汽、奇瑞、大众、奥迪等35家主机厂达成合作,量产定点覆盖数十种车型。
补齐短板
2020年前后,全球遭遇“芯片荒”,从手机到汽车、游戏机、安防等行业无一幸免。
彼时,佑驾创新已经开始规模化交付,芯片短缺问题直接威胁到了公司生存。为确保交付,刘国清带领团队满世界寻找现货和高价物料。“一个普通的MCU(微控制单元)芯片,价格从二三十元炒到了几百元,几乎每个客户我们都在贴钱。”刘国清举例,为了确保与车企的合作,公司花费了数百万元去采购限价芯片。通过类似努力,公司保住了客户,之后还和对方合作了更多项目。
缺芯问题让刘国清意识到要补齐供应链短板,“兜底的能力很重要,拿到了项目,就一定要确保能交付”。
为了提升供应链能力,佑驾创新从以下几方面着手:首先,减少对进口芯片的依赖,推动国产化替代。其次,针对供应链中的长周期物料,佑驾创新建立了一套更抗风险的备料机制。另外,拓宽和供应链打交道的方式,刘国清在内部提出要用销售的思维去做供应链,维护好与上游供应商的关系。那段时间,他和团队走访了大量上游供应商。
他对一次采购经历心有余悸。当时一位女同事为了保供,独自飞往马来西亚,半夜在机场与人接头。国内团队非常担心她的安全,但同事说没事,还把接头人的照片发了过来。大家一看更害怕了——黄头发、大金链子,看起来像是缅北风格。“我说你确定没事吧?她说没事,人已经走了。”刘国清回忆。第二天天一亮,这位女同事就带着芯片飞了回来。
通过这些努力,佑驾创新在缺芯期间保住了客户,也提升了供应链能力。“之后,我们基本上没有因为哪个物料卡壳,还引入了很多国产供应商,带来了成本优势,同时与很多合作伙伴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,帮助我们进入下一阶段。”刘国清说。
挑战是持续的。
2023年,新能源汽车行业竞争白热化。刘国清意识到,体系化能力的建设迫在眉睫。
一方面,通过平台化提升研发效率。刘国清发现,平台化思维不仅降低了项目成本,提高了交付效率,还让研发团队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差异化功能的开发上。例如,公司为奇瑞开发的第一款车型,研发投入较高,但到了第八款车型,研发成本已经降至原来的1/10。“对于最终能够活下来的智驾公司,平台化技术是必修课。你必须要及格,不然很难赚钱。当绝大部分项目赚钱时,公司就开始赚钱了。但现在行业里可能大部分公司还处在做一个项目亏一个的状态,这个很不健康。”刘国清认为。
“智驾赛道人力很贵,毛利率水平又被这个生态的天花板限制住了,要么你能够持续融到钱,资本市场愿意支持你;要么有持续的造血能力。怎么稳健地发展、让研发投入的效率值最高,是我们非常关心的。”刘国清说。
这几年,刘国清变得比以前更爱算账了。从2021年开始,佑驾创新每年年初都会做系统性预算。2022年开始,佑驾创新又引入“项目导入会”,对一些项目进行筛选,“要么现在能赚钱,要么未来能赚钱,要么能在其他地方赚钱,如果没有任何商业价值,我们可能就婉拒了”。
在车企自研智驾技术的趋势下,佑驾创新将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。来源:受访者
“智驾公司研发投入的预算是很难做的,特别是具体到项目,但是必须想办法管控,否则谈何盈利?谈何赚钱?”刘国清强调,现在公司对于费用的管控越来越严。2025年春节开工后的第一个周日,为了弄清楚一个项目的研发投入为何超预算,团队开了4小时的复盘会。平时刘国清也会花大量时间对三费进行管控,包括资金的使用效率、现金流的预测把控、项目的预算和核算等。
成效也正在显现——在保持较高研发支出的同时,佑驾创新研发收入占比出现了明显下降。数据显示,2021~2024年,佑驾创新的研发支出分别为8220.1万元、1.39亿元、1.50亿元和1.56亿元,分别占其总收入的46.9%、49.9%、31.5%和23.85%。
但对于一家要实现盈利或者生存下来的智驾公司而言,这还远远不够。近几年,为了加强对核心技术的掌控,车企加大与智能驾驶产业链公司合作的同时,也开始自研。在车企自研智驾技术的趋势下,佑驾创新将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。
在刘昕看来,佑驾创新在去年的上市非常关键,“相当于鲤鱼跃龙门,这时候它面临的竞争是和其他龙的竞争,是跟其他上市公司的竞争”。战略上,选择哪些合作伙伴紧密合作;战术上,如何持续拿到更多车型数据,持续演进和迭代,都是佑驾创新接下来要应对的不确定性。
东方富海合伙人周绍军也认为,上市后意味着公司实力更强了,但挑战也随之而来。
“短期来讲,香港资本市场对业绩的要求很高。你在资本市场上的价值能否体现出来?定点车企会不会越来越多?收入规模能不能有较好增长?今年或者明年某个时点能否实现盈利?这些都是上市以后,资本市场、投资人会给到企业的压力。”周绍军说。








